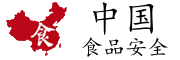和人一样,混的圈子多了,走的地方多了,名字也会多起来的。茶实在是植物中混得最有身份、最有文化、造型最酷的,名字大概也是最多的。
茶最早的名字叫“荼”,苦菜也叫“荼”。陆羽认为《诗经》“谁谓荼苦,其甘如荠”说的就是茶,但农学家一般认为说的是苦菜。跟“荼”相关的名字叫“选”,这个字应该有个草字头的,字库里找不到。“选”是“荼”的别名,如果《诗经》里的荼是苦菜的话,那么“选”也就不是茶的名字了。
“檟”一般认为是比较早的茶的专用名。《尔雅》云“檟,苦荼”,曾有文字学家认为“苦荼”两个字是为“檟”注音的,那这个字应该读作gǔ,但更主流的意见是这个字读jiǎ,也写作“榎”。gǔ与荼的读音相近,而jiǎ与茶的读音相近。我比较倾向于读jiǎ。
“荈詑”这个名字出现在司马相如的《凡将篇》里,这篇记的都是各种药名。八卦一下,司马相如病消渴,小道消息说这个病可能与卓文君太漂亮有关。既是消渴,必须喝茶来解渴啊。“荈詑”后来也分开来用,都指茶,荈是粗老的茶。
“椵、葭”都作过茶的名字,很显然是从“檟”演变而来。四川有个地名叫“葭萌关”,就是《三国演义》里张飞大战马超的地方。“葭萌”也是茶的名字,这个名字后来分成了两个,“葭”与茶近音,“萌”则演变为“茗”。所以中国人卖萌由来已久。
“茗”由“萌”而来,“萌”是指芽叶初生,所以后来高档的喝茶叫品茗。晋郭璞云:“早采者为荼,晚取者为茗,一名荈。”这个说法很快就被反过来了,原因不清楚。
“皋卢”也是茶名,也写作“瓜卢”。皮日休《吴中苦雨因书一百韵寄鲁望》:“十分煎皋卢,半榼挽醽醁。”这个名字后来神奇地音转为“苦丁”,只是不知是否是皮日休喝的“皋卢”。这名字在日语里还偶有出现。
上面说的都是茶的大名,下面来说一下茶的浑名。
“甘露”,这是南北朝刘宋时期豫章王子尚给起的名字。他和新安王子鸾一起去拜访昙济道人,昙济道人给他俩上茶。子尚品味再三说:“此甘露也,何言荼茗。”后来唐朝很传奇的蒙山顶上茶就叫“蒙顶甘露”。
“酪奴”,南齐王肃逃到北魏做官,魏帝问他南北饮食的优劣,王肃说“羊比齐鲁大邦,鱼比邾莒小国。唯茗不中,与酪作奴”。这一自贬的说法,在当时还挺风雅的,彭城王请他吃饭,说:你明天来我家,我请你吃邾莒之食,也有酪奴。
“水厄”,西晋王濛爱茶,并推己及人,所有来他家的客人都要灌之以茶,所以同僚朋友都把去他家当成一件头疼的事,遇此事便称“今日有水厄”。一百多年后,上面说的那个王肃初到北魏,北魏的元义请他吃饭,很文雅地问他“水厄多少”,王肃摸不着头脑说“我从没被水淹过啊”。可见此典故在南朝已经被人遗忘。
“苦口师”,这是皮日休的儿子皮光业给起的。某日,皮光业的中表兄弟请他品赏新柑,并设宴款待。皮光业一进门,对新鲜甘美的橙子视而不见,急呼要茶喝。他手持茶碗,即兴吟道:“未见甘心氏,先迎苦口师。”
“叶嘉”,这是苏东坡给起的。苏学士有一篇文章叫《叶嘉传》,叶嘉者,嘉叶也,这是一篇寓言散文,以茶自况。此文写的是武夷茶,虽然与今日岩茶不是同一类,但也可以了解一下。
“圆月”或“团月”,缘于卢仝的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》“手阅月团三百片”,可能在卢仝之前也有人写过,但谁让卢仝这首诗脍炙人口呢。苏东坡游无锡惠山,曾写下“独携天上小团月,来试人间第二泉”的句子,团月的典应出自卢仝。
“露兄”,宋米芾有诗“茶甘露有兄”,明崇祯年间,一个茶痴开茶馆,以玉带泉,烹兰雪芽,汤以旋煮,无老汤,器以时涤,无秽器。才子张岱即为其馆题名“露兄”。
“雪乳”,陈明远作东陵壶,铭曰“仿得东陵式,盛来雪乳香”。雪乳是宋元点茶的特点,陈明远那个时候喝的是芽茶,借个名而已。
这是增补以后,依旧没有查书。老夫不仅老了,记忆减退,还越来越懒,疏漏勿怪!
作者:周爱东/江南时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