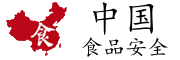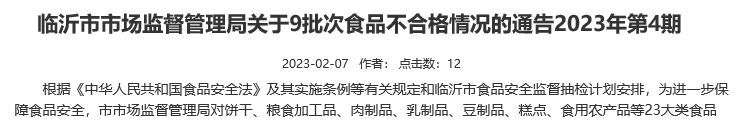□ 何永福
这次随文友们去彭泽县浪溪镇一个叫乌泥冲的小山村采风,途经浪溪水库时,透过车窗,我目不转睛地把绵延数公里、碧波荡漾的浪溪水库看了又看,看不够似的。我之所以对浪溪水库如此感兴趣,是因为她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。小时候去浩山外婆家,要经过浪溪水库,要在水库坐会儿船,坐到对岸后,再走十来里山路,便到了浩山外婆家。到浪溪水库时,已走了约四十里路,腿也走酸了,人也走累了,正是人困马乏的时候,到了浪溪水库,这便有了双重的欢喜。一喜可以坐船好好休息一下,再说我那时坐船的机会不多,甚觉新鲜有趣;二喜坐到对岸后,离外婆家就不远了,胜利在望,不由得让人精神为之一振。
跟大多数人一样,我小时候最喜欢走的亲戚也是去外婆家。但由于外婆家离得远,弯来绕去地有五十多里路,又不通车,得靠走,一般从上午9点左右出发,要走到黄昏时分才能到达,所以,我去外婆家的次数并不多,一年也就正月里随父亲或母亲去趟山里,给外公外婆拜年。当然啰,也不是每年正月都去,父母有时也带大妹或弟弟他们去。由于外公最喜欢我这个大外孙,父母投其所好,带我去的次数自然多些。一听说要带我去外婆家,提前几天我就开始兴奋。
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开始记事时的那年正月随父亲去外婆家,当时我也就四岁左右,年龄很小,是个黄口小儿。记得走没多远,我就走不动了,父亲就得抱着或背着我走。他抱累了或背累了,就把我放下来,让我走上一阵子。记得走到太泊湖水产场时,要走一段湖滩路,湖滩上有许多小河蚬壳,扇形,有大人的大拇指甲大小,白花花的,一小堆一小堆,到处都是。我的小眼睛顿时亮了,这可是能玩的好东西,忙蹲下身来捡,很快就装满鼓鼓的一口袋,我比捡着了宝贝还要开心。捡完蚬壳上了岸,就一直在大坝上走,走完直坝,走横坝;走完长坝,走短坝,总之没完没了。后来,我是彻底走不动了,加上小脚丫迈得又小又慢,很耽误时间,父亲索性就抱着或背着我,不让我走了,他累了就喘口气歇会儿。那时走路的人也多,有个男的从后面追上了我们,他跟父亲很聊得来,跟我们同行了很长一段路。他几次好心要帮着抱我或背我,我认生,任凭他和父亲怎么哄,就是死活不答应。甚至他强行从父亲手里把我夺下,抱起我就走,我还是不配合,在他身上扭来扭去地拧麻花,十分的抗拒。父亲苦笑笑,没办法,还得自己来。好在父亲那时年轻,又身强力壮,能应付得了我这个“甜蜜的负担”。那人只好退而求其次,帮父亲拿包。
我跟母亲去外婆家的次数要多一些,当然,是我大到能自己走长路的时候。母亲身材单薄,力气又小,走那么远的路,她是抱不动、也背不动我的。记得我和母亲常走得额头汗津津、脸上红扑扑的。走累了,我会在心里直埋怨,外婆家咋那么远啊?别人家的外婆都离得近,顶多三五里,抬抬脚就到了,小伙伴们能三天两头往外婆家跑。不过,一想到外婆家那温暖的火塘火,那些好吃的吃食,以及外公外婆亲切慈祥的笑脸,我的怨气很快就烟消云散了,并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。难忘的是那一年正月里去外婆家,母亲带着我和最小的妹妹坐车去的,当时我已经读初中了。坐车去外婆家,走的是另外一条路,路途更远,先要坐五十多里路的车到县城汽车站,再从汽车站转坐八十多里路的车到浩山。那时,各乡镇才通班车,每天往返仅一班,可想而知,能坐上车有多不容易。在我们湖西完小的路口小站,往往是班车一到,车门还没打开,等车的人就迅速地围拢过来,把车门死死地堵住,车门一开,又争先恐后地往车上挤,互不相让,这样就导致下车的人下不去,上车的人上不来,都卡在车门口了。后来司机不在完小路口停车,而是把车往前开一段路后再快速地开门下客。那次我们赌对了,就在班车常停车下客的我们小村路口等,果然如愿,我们几个都顺利地上了车。到了县城汽车站,早就没有座位票了,但好歹买到了几张站票。车上人多,沿途又不断上人,车内因此拥挤不堪,过道上几乎找不到下脚的地方。那时路况又不好,一路坑坑洼洼,车子摇来晃去。我和母亲还好,尽管挤得难受,颠得发晕,但好歹还能看着窗外,分散些注意力。可怜我那才几岁的小妹妹,她就站在过道上我和母亲的腿中间,矮矮小小的人儿,看不到半点外面的东西,路那么长,车又开得晃荡,想想该有多憋屈啊!下车后,我心疼地问小妹妹难受不?不想,她竟一脸天真地笑着说不难受。那次是小妹妹第一次去外婆家,可能是空前的兴奋和喜悦冲淡了她在车上遭遇的磨难吧。
读高中后,我就经常作为家里的“全权代表”,正月里去浩山给外公外婆拜年,有时暑假里也去外婆那住上好几天,大浩山夏夜的凉爽惬意很是让我流连。每次清晨从浩山回家,外公都要走上几里山路,把我送到柳墅那边的车站,等我坐的车开动了,他才放心地离开。每次我都让他不要送,说自己是大人了,可他就是不听,固执得像头老犟牛。
转眼外公外婆已过世多年,加之我的母亲走得更早,唯一的舅舅离婚后又远走他乡,我已很少、竟至不去浩山那边、不去外公外婆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了,但是,也许是人到了喜欢怀旧的年龄,近年来,我频繁地思念起我的外公外婆来,想起他们疼爱我的点点滴滴,去外婆家一度有些模糊的路也因此在心里变得清晰起来。一想到每次去浩山外婆家,当我一脚跨进外公永远在灶下烧火,外婆永远在灶台忙碌的厨房,当我喊一声外公外婆,外公外婆欢喜地应一声“黑毛来了呀”的情景,我就禁不住潸然泪下,湿了眼眶,今生今世,不会再有那两个叫外公外婆的人,对我欢喜地说出“黑毛来了呀”那句再简单不过的话了。